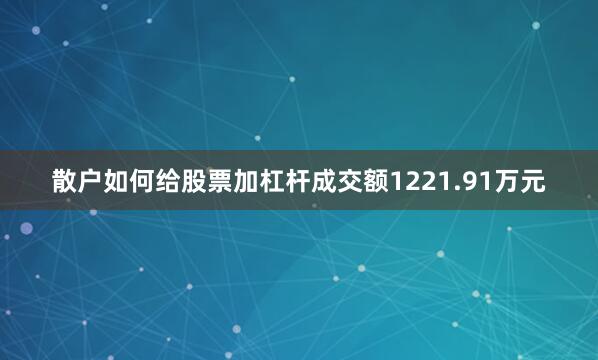作者 | 陈振
来源 | 财经八卦(ID:caijingbagua)

引言:有句话说得好:“发光的不一定是金子,但金子一定能发光。”
在港剧的世界里,一块金劳就是“江湖身份证”。而在2025年的资本江湖里,一块金表也能变成通往港交所的船票。
西普尼——在珠宝界,它不是最古老的名字;在手表界,它也不是最资深的品牌。但它敢用足金做表壳,敢在“珠宝+手表”这个夹缝里拼命生长,就像在钢筋水泥里种下一株黄金的向日葵,要么被踩灭,要么长出金光。

6月3日,中国最大的金表品牌——西普尼(HIPINE)正式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,计划主板上市。而三个月后,它就顺利敲钟了。
这家公司有多特别?它不是卖“时间”的,而是卖“金”的。别人用不锈钢表框装时间,它却用足金装梦想。
它的故事看似闪闪发光,其实是一场关于手艺、时代与家族权力的多重进化。从“打金人”到“打天下”,从新三板到港股,西普尼走了整整十年。

有人说它是“中国的”,也有人说它是“莆田版劳力士”,不管怎样,它确实很有可能变为——资本市场上最有烟火气的金表厂。

要理解西普尼,得从它的发源地——福建莆田北高镇说起。

这个镇子诞生了无数“打金师傅”,在黄金行业里流传着一句神话:十个黄金商人,八个是莆田人,七个是北高的。
北高人靠一把锤子、一块铁墩子敲出了全国黄金市场的半壁江山。从光绪年间南下学艺的张阿罕,到遍布全国的金店老板,这群人靠手艺与耐性,打造了属于草根阶层的黄金帝国。

这群背着小铁锤的北高人,有的在上海开店,有的在北京批发,也有的去了深圳水贝——中国黄金珠宝的“华尔街”。

而李永忠——西普尼的创始人,恰好也是其中一位北高出身的“打金人”。
他1970年生人,2003年中国黄金市场放开后南下深圳水贝。那十年是中国黄金的“盛世”:黄金价格节节攀升,珠宝商遍地开花。

李永忠靠着工匠出身的眼光,创立了西普珠宝,又开了几家公司打基础,正式成为“黄金流通圈”的一员。
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2013年。
那一年,他的女婿胡少华决定“另起炉灶”,成立了深圳尊尚钟表有限公司,也就是西普尼的前身。2015年,老丈人带着两个儿子入伙,全家集结,一锤定音。

从那一刻起,西普尼变成了一个标准的“家族控股公司”:李永忠20.53%,胡少华、李硕、李林茂各13.69%,合计掌握61.6%股份。

老丈人负责看方向,女婿负责打拼,儿子负责执行。说白了,就是“打金的命、做表的心、传家的局”。
他们踩中了时代的节点——从“卖金子”转向“卖品牌”。这在中国黄金行业里,是个关键的分水岭。


西普尼最早并不打算靠“金表”吃饭。
2016年,它以“智能穿戴+高端机械表”双主业在新三板挂牌。那时候,智能手表刚起步,谁都想当“中国的Apple Watch”。
西普尼靠着代工起家,合作客户包括华为、华米,甚至一度靠智能手表拿下公司的大头营收。

但很快,它发现——这不是独属于它的赛道,西普尼必须融合发展。
智能手表的毛利率偏低,而西普尼自己做高端金表的毛利率能翻倍。代工一年,累成狗赚不够几克金。更糟糕的是,智能穿戴是科技红海,烧钱多、估值低、利润薄。

于是2019年,西普尼果断从新三板摘牌,拿到深创投3亿融资后,他们回到了自己最核心的阵地——黄金。
这波操作非常“莆田式”:风口不好飞,那就去挖矿。他们重新定义了目标——不做科技梦,专心做金梦。

西普尼的金表不是老气的那种,而是彻底玩出了“新国表”路线。

旗下核心品牌HIPINE(西普尼)和副品牌GOLDBEAR(金熊)两个品牌,从2000元到6万元,SKU多达一万个。年轻人想买炫的,中年人想买稳的,长辈想买传家的,全都能在水贝门店的展柜里找到对应款式。

传统金表结合珠宝智能穿戴的企业发展方向,西普尼的财报给人眼前一亮:2022财年至2024财年,营收从3.24亿涨到4.57亿,净利润从2500万涨到4900万,毛利率从19.8%爬到27.2%。

这成绩放在制造业算“闪闪发光”,但别高兴太早——西普尼的业绩命门就在金价。
金价涨,消费者犹豫;金价跌,库存缩水。

报告期内,原材料成本占营收七成,全靠黄金撑着。2023年黄金暴涨,西普尼销售成本变高,利润增速只能平平。因为涨价让金表更贵了,但消费者不一定买账。
几天前,金价正式突破1200元每克,再次创造历史新高。这就成了“金表逻辑”的荒诞现实——看似高端,实则被金价牵着鼻子走。

西普尼要想稳住大盘,还得随机应变。

有一句话对西普尼总结得特别形象:“我们做的不是表,是传家宝。”这话既是他们的广告创意的投影,也是股权结构的写照。
自9月30日IPO后,李永忠家族仍稳坐控股地位。胡少华任总经理、李硕任副总经理、李林茂掌生产。这套配置,稳得像黄金,密得像瑞士机芯。

这种“莆田式家族模式”有它的独特逻辑——金子讲究纯度,企业讲究控制权。
家族企业的优势在于执行统一、信任牢固;劣势在于创新迟缓、决策封闭。资本市场喜欢激情,而家族喜欢稳健。
两者的矛盾,就藏在西普尼的表盘下。
如果你看它的股东名单,会发现那股“资本味”终于开始越来越浓。IPO前后,除了深创投外,还有几家投资公司进场。

西普尼正在尝试用“制度化”包裹住“家族化”,让故事听起来更像一个“新国货品牌”,而不是“北高家族作坊”。
李永忠也意识到“金表难卖”的未来。于是他开始学会讲故事:在招股书里,西普尼的叙事变成了“传统工艺+智能制造+文化IP”,一个让资本市场听得懂的混合体。

他们开始请代言人、做联名、讲情怀。这不是品牌转型,是家族企业想学会“讲故事”的觉醒时刻。

但问题是——资本要快,家族却要稳。
老丈人可以稳住生产,女婿可以懂品牌,但资本的游戏是另一种语言——那叫“增长叙事”。而西普尼现在最大的考验,是如何让大众相信已经在港股登陆的它不只是一个金表厂,而是一家“可复利的消费品牌公司”。

这两种节奏能不能合拍,是决定它未来能否从“金表厂”变成“国表巨头”的关键。

金表的故事好讲,但现实骨感。
在高端钟表市场,劳力士、欧米茄、早已扎根中国三十年。人家卖的不仅是计时工具,而是身份、地位、生活方式。

而西普尼卖的是“材质”。消费者买劳力士,是为了在饭局上被人看见;买西普尼,是为了在金价涨的时候心里踏实。
于是,一个神奇的现象:过去,中国人买黄金是为了传家。现在,中国人买黄金是为了保命。

金价疯涨、币值波动,年轻人一边说“黄金自由”,一边默默加仓金豆豆。
这背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。一个是品牌溢价,一个是实物价值。前者靠信仰赚钱,后者靠克数生存。

所以请别误会,这帮人可没打算买金表。
他们要的是“金子”,不是“表壳”。西普尼的难题就在这——它做的不是刚需,而是“装饰性保值品”。

说白了,金表的意义,是让人相信自己“戴得起时间”。可当时间都被手机接管,谁还在乎手腕上那点克重?
在Z世代眼里,金表不是身份,而是“我爸的梦”。
西普尼再怎么努力,也很难让金表成为新的潮流符号。毕竟,现在年轻人更愿意为“科技感”买单,而不是“贵气感”。
当然,也不是全无机会。
在港股市场,“工艺+新消费”依然有想象空间。泡泡玛特靠潮玩讲文化,老铺黄金靠传承讲国潮。

西普尼如果能讲出“国表自信”“黄金智造”的故事,也许真能杀出一条血路。但前提是,它得先从“黄金思维”切换到“品牌思维”。

否则,再闪的金,也只能照亮财报的一页。

西普尼的故事,本质上是一部“打金人上岸史”。
从北高的锤子到水贝的工厂,再到港股的敲钟上市,这家公司代表了一整代中国制造者的进化。它让手艺人有机会敲响资本的钟声,让“金匠精神”有了闪耀的舞台。
但资本市场讲究时间,而手艺人讲究耐心。一个靠黄金起家的品牌,能否在股市上走得稳,还要看它能不能从“卖材质”转向“卖价值”。

西普尼此刻站上了港交所的舞台,手里握着的不仅是一块金表,更是中国民营制造业的集体梦想:从工厂到品牌,从代工到自营,从财富到信仰。

只是这一次,钟声响起后,长久来看,是不是金光万丈,还得交给时间来回答。
对此,您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,发表您的意见或者看法,谢谢。

实盘股票杠杆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深圳股票配资论坛高关税必然会招致外国的报复
- 下一篇:没有了